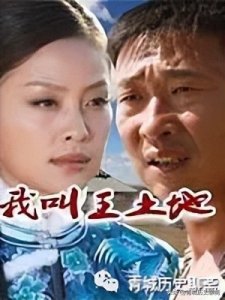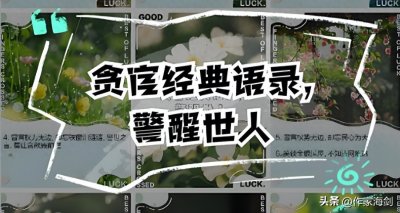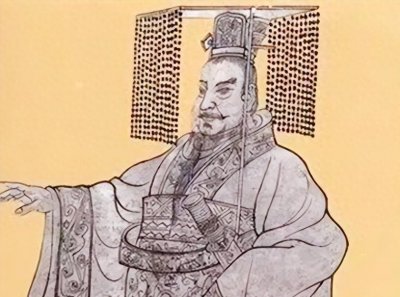【我在民勤一中读书的日子】马婧:最好的我们
【我在民勤一中读书的日子】马婧:最好的我们
看着母校公众号里连载的【我在民勤一中读书的日子】,几次蠢蠢欲动想写一写关于我在一中的点点滴滴,提笔时又觉得自己文辞粗浅,所记之事细小琐碎,但这些对于我来说,又是难以忘怀且无法复制的青春年华……
迟到风波
上一中时,同学们私下里都习惯把老师称为“爷”。“武爷”是王立武老师,四十多岁,是我的班主任老师。当时怕武爷,其实最怕的是上学迟到了被武爷抓住挡在楼道里罚站。每天早晨,闹钟总是“叮铃铃,叮铃铃……”一遍又一遍的响,母亲总是一遍又一遍催促着我起床,而我还沉浸在梦里,丝毫不想和我的床分开。直到时间逼近上学的临界点,我才火速起床洗漱,时间宽裕的时候还能吃一碗母亲准备好的牛奶或者豆奶粉泡馍馍,而很多时候则是洗漱完骑上自行车就跑。穿过小巷穿过步行街,车速真的是只能用“飞快”来形容。我觉得从初中的小胖墩瘦下来完全是每天赶时间骑自行车的功劳。然而骑这么快肯定避免不了出意外。冬天的早晨天分外黑,广场上、马路上的路灯都没有亮,路上少有行人,来来往往的都是披星戴月的老师和学生。口罩帽子全副武装后,上学的路上确实暖和了不少,但是对于近视的我来说却不太友好,它们几个根本没有办法和平共处,戴上口罩眼镜一片模糊,更看不清了,取舍之下就放弃了眼镜,真的是在摸黑前行。记得最危险的一次是黑咕隆咚地撞上了停在步行街上的小货车,自行车车把也被撞歪了,但是时间紧急,根本顾不了太多,简单靠在路边借助道牙子扳正车把,在不影响骑行的情况下,就又踩着向学校奔去了。好在当时汽车相对少,步行街上也不允许汽车通行,否则我这样“风驰电掣”必然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在路上常常还能遇到一起赶时间的小姐妹,一般会在步行街遇上石倩,在天桥巷口子遇上欣怡,然后便是一起“飞”进校门,推着车子在校园里狂奔,而一般这个时候已经没有空位了,只能将车子随处一塞,有时候根本来不及锁,此刻最重要的是马上进教室然后若无其事地坐下来开始早读。但有的时候压根就找不到车位,只能偷偷将自行车停在实验楼北侧老师们停车子的地方。放好车子,赶在最后一声铃声响的时候跑到教室。真的很感谢当时的音乐铃声,大概能响一分钟,往往是进校门的时候听见早读的铃声开始响,到教室门口铃声刚落。后来武爷终于忍无可忍,把我们几个老是踩着铃声进教室的同学挡在了楼道里面以示警戒。有一次中午上课的预备铃响了,教室里还有很多空的座位,离上课还有几分钟时,我们几个走读的,还有住校的同学,才分别从教学楼的正门和侧门跑了进来,毫无悬念,我们被武爷挡在门外狠狠批评了一顿。此后,就再也不敢踏着铃声进教室了,大家都会准时进校门。
我的学霸同学们
长相平平,成绩平平,工作平平,但至今仍让我吹嘘的就是我有一群名校毕业的学霸同学。
2009年开学报道第一天,最开心的莫过于看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初中同学、小学同学,又和我成了同班同学。我和常哲更是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同班,而且前后桌,还有欣怡、王磊、石倩、柴琪、王建业……最好的朋友都坐在一起。现在想想,那不就是最好的我们吗?一起上课,一起追逐嬉闹、谈天说地、细数着毕业后要做的事,一起去三味堂吃牛肉面、在冬日的暖阳下绕着操场压马路、趁着仅有的课间10分钟跑去小卖铺买零食、晚自习结束回家的路上在大眼睛阿姨那里吃烧烤……点点滴滴,都在2012年6月8日下午“考试结束,请考生立即停笔……”的广播声中画上了句号。
当时我们一个年级全县有6000多学生,竞争比较激烈,同学们都很上进,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当时我们班的尖子生们已经很内卷了。平常除了要上交的配套练习册和作业本,老师们好像没有给我们布置过什么硬性作业,大家都是根据自己的情况买一两本课外练习册巩固。当我这个菜鸟一份练习都勉勉强强啃完的时候,我们班的学神们早已刷完了好几套试题。睡眠不足是高中生的正常现象,而我更感觉自己是瞌睡虫附身了,一回到家坐在桌子前,做不了几道题就趴桌子上睡着了,所以为了提高学习效率,我就跟着住校的同学们上第三个晚自习,周末也是,尽量在学校学习。但就算是周末、假期,都能在教室、自习室、阅览室看见我们班的同学们专心学习、认真阅读的身影。

记得有一年的寒假,大概有一半的同学都会坚持每天在学校学习。努力自然是有收获的,同学们最终也都考得挺好的,发挥失常的同学在补习一年后也都考上了理想的大学,最终大概有一多半都考上了985/211。而我,可能根本就不适合学理科吧,尽管班主任是物理老师,我的物理成绩也是极差,算是倒数的那种吧,真的太辜负武爷的谆谆教导了。现在想想,当时硬着头皮学理科,无非就是不想离开熟悉的圈子、熟悉的同学,更不想舍弃实验班这个头衔罢了,再加上听了太多“学理走遍天下”的大道理,也没有考虑太多的兴趣爱好,只是按部就班地跟着大部队的方向前进。当然我的成绩也是意料之中的一路下滑,从进校时的60名开始暴跌。好在在老师的精心指导下和周围同学们的热心帮助下,最终以全校一两百名的成绩考入了一所四流985收场,也算是没给班级拖后腿吧。
虽然我们班学霸众多,但同学们并不是只知道读书的书呆子,大家爱好广泛且卓越,极具音乐天赋的柴琪,唱歌、古筝、钢琴样样精通,是我们班在艺术节上的扛把子;画画超棒、还会跳舞的欣怡;书法达人袁洁,电子琴能手魏侨,吉他王子孙文;会拉二胡、吹葫芦丝的常哲,喜欢唱歌的杨家旺、唐铭轩、连立潇,博古通今的尹杰、孙阳、王泳钧等;写一笔好字的更是数不胜数,大家的字体各有各的风格,有的字迹苍劲有力、沉着稳重,比如张治文、马俊琛等同学的,有的柔美秀丽,如何欣怡的,有的方正严谨,好似印刷体,如常哲的,有的清秀工整,如潘雪梅、谢晓惠、陈晓月、李倩、王静等的,字如其人,个个都是文静温婉的女生。体育运动方面也是人才辈出,篮球场上所向披靡的潘国鹏、甄洋、严培谦、张衡、张治文、魏鑫磊等;乒乓球健将刘璐、石倩、魏乔、俞振山等;足球队更是人才济济、阵容强大,王磊、杨家旺、王建业、孙文、唐铭轩、陈泽业、刘发瑞、王泳钧、潘越、王海明、张鹏等个个身怀绝技,他们分工明确、协作配合,总能赢得一场又一场激烈的比赛,但偶尔也会出现被碰得鼻青脸肿在楼道里罚站的小插曲。在这里还要说一下学识与身高齐头并进的小孙阳,早早就通过竞赛保送了,于是在我们埋头苦练的时候,他就很悠闲地进入了半大学模式,他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文理兼修,每次会带来很多杂志,印象最深刻的是《大学生》,新的一期刚出来我们都争相借来看。也是通过他,我和同桌晓月才知道图书馆的书原来学生也可以外借,周六晚上还可以去三楼的阅览室看最新的杂志和报纸。当时班里传阅最多的有女生们喜欢看《疯狂阅读》《意林》《青年文摘》,男生们爱看的《南方周末》《环球时报》《特别关注》,还有当时流行的青春伤痛文学《萌芽》《最小说》等。

当然,90后的我们也是将调皮捣蛋、非主流、叛逆的标签刻画地淋漓尽致,所以我们也是令老师们头疼的“最难带的一届学生”。自习上夹在练习册里的杂志、小说、小纸条,从校服袖子穿出来的耳机,运动会期间风靡的三国杀,还有节假日的网吧、台球室,都在被抓、被没收的边缘疯狂试探。课间或是趴桌子睡倒一片,或是同学们聊天吵吵闹闹,当然也有风风火火的。记得有一次课间,教室里大家千姿百态,还有奔跑和跳跃,武爷气的说我们是在群魔乱舞。再加上我们当时人多,我们60多个人的班级已经算是小班了,后面英才楼据说都是80-100多人的大班,管理难度可想而知。现在想想,当时老师们每天面对着黑压压的人头,如果讲课或者自习的时候再夹杂着同学们叽叽喳喳的讲话声,估计心中的怒火早已熊熊燃烧了。
最好的老师们
很庆幸初中高中都在实验班,可以说是一直享受着全县最优秀的师资力量。老师们和爸妈年纪相仿,大多是90年代的中师生,是在当时贫瘠的教育环境之下成绩最优异的那一批人,他们心怀家国天下,把教书育人作为自己一生要践行的伟大使命,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物理老师“武爷”是班主任王立武老师,数学老师“茂爷”是二班的班主任卢茂林老师,语文老师“军爷”是三班班主任常晓军老师,英语老师“钧妈”则是我们班王永钧同学的妈妈……老师们认真负责,又张弛有度,他们理解尊重我们的成长速度和个体差异,给了我们自主学习的权利,大家都是根据自己的情况自行刷题,不懂的再请教老师,这种学习方式真的是让我们终身受益。武爷更是充分尊重我们每个人的学习方法,所以我们自习的场所不限于端坐在教室,瞌睡了可以在教室里站起来背书,也可以出去在教室外面、凉亭里、长廊里,晚读也可以去报告厅听专题讲座。总之,只要学生们认真学习,他总是支持的,但肯定也少不了不定时、无死角的监督巡查。

每个老师的讲课风格也各有特点,武爷讲课跌宕起伏,走到实验楼就能清晰地分辨出他在哪个班上课;茂爷则是风趣幽默,一个眼神一句话就能让沉闷的课堂瞬间活跃;军爷教语文真的是再适合不过了,有种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儒雅气质与师者风范,大家最喜欢的大概就是军爷的课了,意气风发、挥斥方遒,他讲授的不仅仅是语文,更是文学和哲学,可以从诗词古文讲到人生百态,也可以从文学小说讲到社会现实,让我们更宽广地认识了这个世界。我们也最期待每次作文本上军爷给的评语,这是对我们写作的鼓励更是认可。生物仲作军老师更是把课本装在了脑袋里面,可谓满腹知识,上课从来不拿课本,在教室过道里面一边走一边讲,昂首阔步,气宇轩昂,保证每位同学都能清楚听到,他自信、乐观、饱满的状态也深深地感染着我们每一个人。另外,老师们都有着扎实的板书功底,行云流水又铿锵有力,最佩服的就是武爷和茂爷的徒手画圆,堪称一绝。
小黑屋的三年
原本教室会随着年级逐渐升高,然而我们那一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教室一直停留在育才楼一楼。一楼进出极其方便,课间可以出去透透气,看看窗外的丁香开了几朵,甚至可以踢一踢毽子活动一会儿。赶上下午是活动课的时候,男生们更是借助着一楼的地理优势,提前几分钟就抱着球守在教室门口,下课铃一响便冲出教室去抢占场地。
但是一楼也有弊端,教室的第一个窗户那儿是个抬高的花池,于是乎,晚自习上经常会在这里看见武爷、钧妈和部分家长们盯梢的身影。还有教室外面的刺柏、樟子松、丁香、柳树总是把光线遮挡的严严实实,尤其在冬天,大部分时间教室里光线都不太好,得开着灯学习,这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不少困扰,戴眼镜的同学陆续增加,眼镜度数也日渐上涨,同学们和家长们都多次提出搬教室的请求,然而最终也没有实现。我们在小黑屋一待就是三年,直至毕业。
一毕业学校就装修
我们也未逃过“一毕业学校就装修升级”的命运,2012年毕业后,曾经承载着我们青春记忆的育才楼拆了,实验楼也拆了,水泥操场铺上了塑胶,后来新的教学楼建起来了,但是却没有了再次走进一中校园的理由,总感觉回忆被偷走了一块,空落落的。好在毕业那年的十一假期又来到一中,拍下了属于我们的最后回忆,看着即将被拆除的教学楼,心中不免有些伤感和惋惜,但还是由衷地希望母校越来越好。
这便是现在每每想起都能嘴角上扬的高中生活了。
高中毕业之后我们各奔东西,大家奔赴不同大学,但庆幸还能在假期见一见。工作之后,大家能聚在一起的机会好像越来越少了,再加上这几年疫情影响,大家回家受到各种艰难险阻,相聚更是难上加难,就祝愿大家在各自的城市一切安好。
最后以谢伟同学改写的歌词《东小十字的日子》结尾——
当某天,再踏进,这校园会是那片爬山虎,牵着回忆的流年
表示从教室到三味堂的距离,原来只有三年
表示钧妈武爷茂爷立祥很有爸妈脸
各种磁场立几全都搞不懂,还有定状补
各种曾经没收的小说P3,如今又打开
我们穿上正装假装成长,数码挥霍习惯的笑脸
悲伤一发,寂寞唏嘘痛的初体验
毕业的字眼,格外扣人心弦,各种莫名的感伤,只说一句,我去,你装

作者简介:马婧,民勤一中2012届校友,2016年毕业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林专业,同年就职于金昌市农艺研究院工作,园林工程师,现在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研修学习。
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