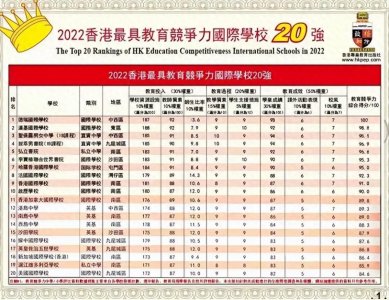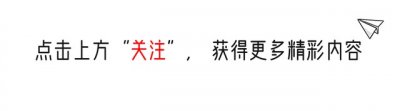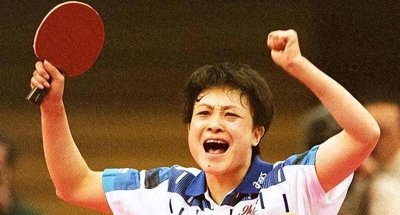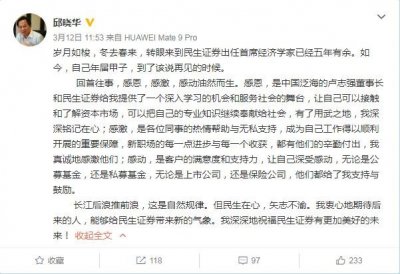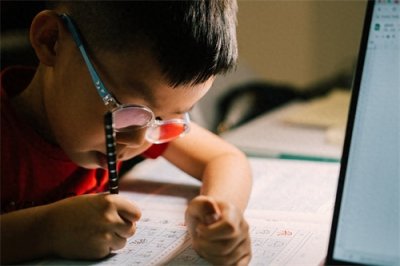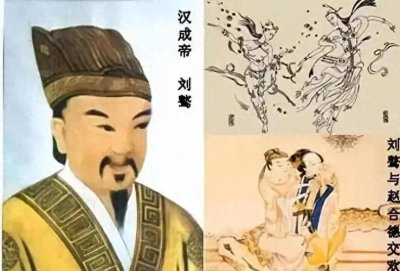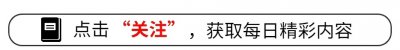中世纪法国狂欢节中的“加冕”仪式,及其特征和意义
中世纪法国狂欢节中的“加冕”仪式,及其特征和意义
#历史开讲#
加冕礼是一种就职仪式,通过这一仪式,王位候选人加冕称王,从而拥有了新的身份和职责。而狂欢节之王则是从各大游戏社团的领导者中间选出;被选出的社团领导人通过戏仿的加冕仪式,成为新的狂欢节之王。
“加冕”狂欢中的“颠倒”特征
法国青年游戏社团“傻瓜社团”的领导人“傻妈妈”就是经过选举成为了狂欢节之王。在法国北部,狂欢节之王还有年龄上的区分:不同的年龄层选举专属各自年龄段的狂欢节之王,如“孩子之王”和“青年之王”等。
经过评选产生的“假国王”为了展示自身的权威,通常会在选举之后骑着马绕街游行示众。这种行为的典型代表者是被称为暴徒的狂欢节之王——亨利;亨利在当选节日之王后,表现出了举止行为都极尽夸张的游街行为;戴着面具的亨利骑在马上,身后是在他的命令下扮成商人、律师等不同职业的仆从;在巡视的过程中,他还不停地挥动手中的皮鞭,装作在抽打随从的样子。

凡此种种,皆是为了树立自身的威信,以便在狂欢节当天做一个受人敬仰、尊崇的“国王”。与真正的国王一样,狂欢节之王的人选必须是得到人们拥护和支持的人,故而纵然有人在狂欢节将自己装扮成节日之王,也没有什么意义,更不被人承认。
此外,在中世纪法兰西的愚人节中,也有将下层教士及唱诗班的男孩选为“主教”或“大主教”的庆祝方式。将教会下层神职人员或唱诗班的男孩通过神圣戏仿的形式选为“主教”或“大主教”,这虽然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加冕”仪式,但却也具有加冕仪式的某些特征,因为下层教职人员被选为主教后,会头戴主教法冠,手持权杖,胸前佩戴着十字架,受到人们的拥戴。
“愚人节”为下级神职人员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即人们用开玩笑的方式对教会的神圣仪式进行模仿。最为关键的是,在此期间,正常的教会事物都被打乱了,而下级教职人员们的举动则变得疯狂,1264年法国北部城镇圣奥梅尔在割礼当天庆祝这一节日时便阐明了这一切。

期间,愚蠢的“主教”和“院长”参加了这一节日活动;后者穿着滑稽的服装焚香致敬;整个办公地点充斥着吟唱甚至嚎叫的声音。1445年3月12日,由巴黎大学神学院的院长发起,该院向法国的主教和主教会议题写了一封信,而从起诉书的细微之处来看,这是关于愚人节的一系列相关文献中最令人好奇的一部分:它包括一篇序言和至少十四条结论;序言列出了有关愚人节的一些事实,而神学家称这些行为在异教仪式中有明显的先例。
因为“在办公时间,人们可能会看到牧师和神职人员戴着面具装扮怪异;他们扮成女人、游吟诗人或皮条客在唱诗班中跳舞,并肆意唱着放纵的歌。当主教在做弥撒时,他们则在祭坛的角上吃黑布丁,并在那里玩骰子。焚香炉里冒着浓烟,里面燃烧的并不是香料,而是旧鞋底。
他们在教堂里嬉戏打闹,丝毫不为自己的不雅行为感到羞愧。最后他们会乘着破旧不堪的马车绕着城镇和戏院游行,用不雅的表演、下流的姿势和粗俗的话语来逗乐同伴和围观者。”上述种种行为表明,在愚人节期间,教职人员的所作所为与其平日里循规蹈矩、寡言克制的形象截然相反。

“悼婴节”或称男孩节,是唱诗班儿童们的节日。该种节日一般在法兰西地区庆祝,而罗恩则是庆祝这一节日的典型地区。“男孩节”包含了很多有趣的细节:在圣约翰节的第二次晚祷后,男孩们两两结伴,走出教堂的法衣室,并和他们的“主教”一起唱着圣歌;向着悼婴节的祭坛出发,接着便由“主教”开始赐福仪式;主教的功能被明确规定—他穿着丝绸束腰外衣和长袍,戴着法冠,手持权杖,但没有戴上戒指。
男孩们向他行礼,就像对着真正的主教行礼一样;“主教”行使神甫的职责,一直持续到宴会结束,当然除了做弥撒之外;他在第一次晚祷的赞美诗结束之后,开始赐福。尽管唱诗班的男孩相较成人教士更容易服从管理规训,但这一活动也因自身很多违反习俗惯例的行为而被谴责,且已经被不止一次控告过,只不过人们控告的通常是其间不甚重要的事情而非严重的犯罪行为。
在愚人节中,教会人员除了对下层教士和男童进行“加冕”之外,也会对驴进行加冕,并举行与驴相关的各种庆祝活动,例如中世纪法兰西的鲁昂、桑斯地区就曾举行以驴为主角的游行仪式。关于驴节的举行不只发生在街道,有时也发生在教堂内部。教职人员在节日当天集聚教堂,将祭祀用的被子披在驴的身上,对其进行“加冕”。之后,为了进一步增加节日的戏谑效果,教堂内的人们还会对着这头被“加冕”的驴进行祈祷。

在13世纪桑斯主教编写的日课经中,还有邀请人们通过对驴的叫声的模仿,向驴致敬的内容。在加冕仪式的狂欢活动中,普通民众和下层教士加冕成王,模仿国王及主教的行为进行管理,实际上也代表着一种“颠倒”。
这种狂欢性的颠倒不仅体现在职位上,而且还体现在狂欢节庆期间的服饰和食品上。在中世纪,服饰是区分性别、年龄以及身份地位的重要手段。然而,这种界限在狂欢节中被彻底打破。在节日期间,人们反穿、串穿衣服的行为屡见不鲜。塞巴斯蒂安·弗兰克就曾在1534年提及狂欢节中人们穿着混乱的现象:“男人将女人的‘裙子’穿在身上,而女人则穿着男人的衣服,看上去十分怪异”。

1605年,一首关于狂欢节的歌曲中也唱道:“这个山头,男扮女装,那个山头,女扮男装”。除了男女服饰穿着上的混乱之外,还有年轻人穿老人的衣服、贵族扮农民、农妇摇身变成贵妇人等行为。威尼斯的贵族桑努托日记中的内容就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最好的注脚:“不少人会穿上标志着贵族身份的酒红色天鹅绒长袍,并将仿照总督服装样式制作的装饰物戴在身上,此外,还有人模仿政府大总管挂上金色的项链”。
食品价格乱套也是狂欢节的另一重要特色。在这期间,商品的价格的贵贱秩序被颠倒过来,例如在标志着罗芒狂欢节的圣布莱兹节里,就是这样一番情景:“葡萄酒和甜食的价格低廉得几乎等于分文不取,而熏鲱鱼却贵得无人敢于问津”。
而且因为节日持续时间非常短暂,“奥克西塔尼的这个地方似乎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一个安乐之乡,最要紧的事就是吃,连古堡都是用甜点制作的。”在狂欢节期间,所有的消费都极尽奢华之能事,任何地方都“无法无天”。
标签: